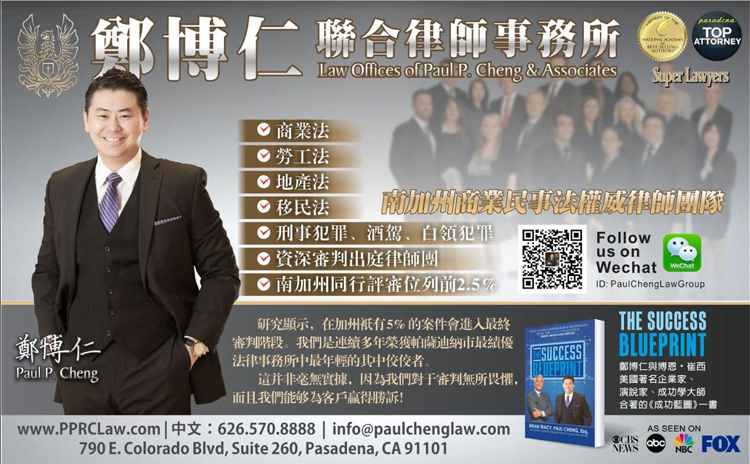2016年12月7日 星期一
《紐約客》:扎克伯格 從天使到魔鬼只有一步之遙
來源:財經十一人

2018年4月11日、12日,扎克伯格分別參加美國參衆兩院的聽證會,合計10小時。他對議員們說:“僅僅把人們連接在一起是不夠的。我們必須確保這些聯繫是積極的。我們有責任不僅爲人們提供工具,而且還要確保這些工具被用來做好事。”
在言論和真相之間,扎克伯格選擇了言論;在速度和完美之間,扎克伯格選擇了速度;在規模和安全之間,扎克伯格選擇了規模。到目前爲止,他的生活使他確信他能解決“一個接一個的問題”,無論公衆可能就此發出怎樣的嚎叫
Evan Osnos | 文
韓巍 | 譯
8月,一個工作日的上午10點,Facebook主席兼CEO馬克·扎克伯格打開了家裏的大門,面帶程式化的微笑。他不喜歡採訪,尤其是經過兩年無休止的爭議和聽證之後。
他走向廚房,廚房裏有一張長長的原木桌子和青綠色的櫥櫃,他說,“我還沒吃早餐。你呢?”
2011年以來,扎克伯格一直住在加利福尼亞新月公園(Crescent Park)附近一個有着百年曆史的白色板房裏。住宅小區被繁茂的橡樹環繞,距離斯坦福大學不遠。
這座耗資七百萬美元的房子給了他一種安全感。房子離大路有一段距離,隱藏在籬笆,牆和茂盛的樹木後面。客人通過拱形木門進入,沿着長長的礫石小徑前往前面的草坪,中心設有游泳池。
在扎克伯格買下房子後的第二年,他和相戀多年的女友普麗西拉陳在後院舉行婚禮。後院有花園,池塘和陰涼的亭子。
後來,他們有了兩個孩子,並在夏威夷買了一座700畝的莊園,在蒙大拿州買了個滑雪勝地,在舊金山的自由山上購置了四層住宅。但這家人平時就住在這裏——距離Facebook總部只有10分鐘車程。
有時候,扎克伯格會在後院或餐桌上錄製一個Facebook視頻。
雖然扎克伯格是他這一代人中最著名的企業家,但他並不熱衷於社交,除了一小部分親友外。對於媒體和公衆來說,他難以捉摸,但他對自己隱私的極度保護,反而增加了公衆的窺探欲。
當地媒體曾記錄了他與一位開發商的糾紛。後者計劃建造一座可以看到扎克伯格主臥的豪宅。經過漫長的法律訴訟後,開發商放棄了,扎克伯格花了四千四百萬美元買下他周圍的房子。
創業多年,他已經清楚知道,自己作爲公衆人物需要經常接受來自各界的批評。畢竟,Facebook的業務,“位於技術與心理學的交匯點,而且和每個人息息相關。”
扎克伯格的求勝慾望
他帶着一盤香蕉麪包和一瓶水進入客廳,然後坐在海藍色的天鵝絨沙發上。
自2004年創辦Facebook以來,他的制服從連帽衫和人字拖升級到現在的服裝,灰色毛衣,靛藍牛仔褲和黑色耐克鞋。
三十四歲的扎克伯格皮膚非常白皙,前額高聳,眼睛很大,比十多年前第一次成爲公衆人物時更爲精幹。
比起看電視,他和他的妻子更喜歡桌面遊戲,而且在沙發夠得到的範圍內,我注意到了一款名爲Ricochet Robots的遊戲。
“它極具競爭力,”扎克伯格說。 “我們和這些朋友一起玩,其中一個是天才。和他一起玩真是生氣啊。“
Dave Morin,前Facebook員工,作爲創始人和CEO創辦了一家尋求治療抑鬱症的創業公司Sunrise Bio,他曾經在辦公室與扎克伯格一起玩Risk桌遊。
“他不會玩一局就罷休。“莫林告訴我。 “第一場比賽,他可能會把他所有軍隊聚集在一個戰區裏,而下一場比賽他可能會將士兵們排滿整個戰場。他試圖找出在所有比賽中擊敗你的心理方式。”
扎克伯格這種強烈的求勝慾望,在科技圈人盡皆知。
Dick Costolo,Twitter的前CEO對我說,“他是一個無情的執行機器,如果他決定來和你競爭,你就會受到毆打。”
LinkedIn的創始人裏德霍夫曼說:“硅谷有很多人,對馬克有共識,他非常具有攻擊性和競爭力,所以有人對他頗有些看法。“
霍夫曼是Facebook的早期投資者,但很長一段時間,他都感覺到扎克伯格在和他保持距離,因爲他們都在搭建社交網絡。
“‘你的LinkedIn會被幹垮,所以儘管我們很友好,但我不想與你親近,因爲我要幹垮你’,現在,當然,這已經過去了,我們是好朋友。”
不過,扎克伯克是這麼迴應的,“對於任何社交網絡而言,如果想要順利存活下來並且繁榮發展下去,都得依網絡效應。只有不斷擴大用戶基數,網絡效應帶來的價值才能實現快速增長。所以,如果Facebook想要順利實現自己的發展願景,僅僅開發出最優秀的業務功能是不夠的,我們必須要構建起一個最好的社區。沒錯,我渴望成功,所以有時候你必須打敗某人,但這(打敗對手)並非我的初衷,也不是我的慣常做法。”
多年來,扎克伯格在Facebook會議上,頻繁用到“主導”(Domination)一詞。
但自從知道歐洲立法體系將該詞定義爲“企業壟斷”後,他便不再把這個詞掛在嘴邊了,但是,他顯然從沒準備過接受失敗。
幾年前,他和朋友的女兒一起在公務機上玩拼字遊戲,當時她正在讀高中,她贏了。
接下來的第二場比賽之前,他寫了個簡單的計算機程序,可以在字典中自動搜索詞彙,提高自己的贏率。
當飛機降落時,扎克伯格的程序小幅領先。這個女孩告訴我,“在我和程序遊戲比賽時,我們身邊的每個人都在站隊:人類組和機器組。”
超級帝國Facebook
如果Facebook是個國家,它無疑是世界第一大國。高達22億的月活用戶,約佔全球人口的三分之一,擁有與基督教一樣洶涌的追隨者。這個用戶基數在美國企業史上沒有先例,
幾年前,該公司仍然熱衷於展示實力。通過收集大量有關用戶的信息,它允許廣告商精確定位人羣,這種商業模式在一年內讓Facebook的廣告收入超過所有美國報紙的總和。
扎克伯格花了大量時間與國 家元首商討並公佈了雄心勃勃的計劃,例如建造巨型無人機,將無線互聯網(包括Facebook)引入發展中國家等。
他熱衷於掌控公司;除了擔任董事長和CEO,他還控制大約百分之六十的股東投票,這依賴於投票權十倍於普通股的優先股。他的個人財富已經增長到600多億美元。
Facebook是主導互聯網的四家公司之一(連同谷歌,亞馬遜和蘋果),它們市值之和大於法國的國內生產總值(GDP)。
但於此同時,用戶數據隱私問題以及Facebook對用戶行爲的影響問題,一直飽受公衆輿論指責。
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期間, 它就已經遭到了傳播不實信息、導致社會動亂的指控。
有些人操控利用了Facebook的自動系統,用“虛假新聞”釋放有毒的政治誘餌。至少有一百個網站被追溯到馬其頓小城韋萊斯,支持川普的Facebook羣組流量總是 處於高峯。
假新聞源也向Facebook支付了“微定向”廣告,這些廣告面向的是容易洗腦的用戶羣。
另據美國情報部門稱,其它行動罪魁是俄羅斯特工,後者通過製造政治混亂幫助川普獲勝。
今年2月,負責俄羅斯干擾美國總統大選的調查專員Robert Mueller,指控了13名俄羅斯人使用Facebook,Twitter和Instagram進行“干涉行動”,花錢投放中傷希拉里·克林頓的廣告,從而影響民主黨派人士的投票決定。
根據預估,這場干涉行動效果驚人,不到一百名特工,觸達操縱了一億五千萬用戶。
甚至還有一些公司的前高管跳出來,公開批評Facebook加劇了分裂,煽動了公衆情緒。
去年發表在“美國流行病學雜誌”上的重要研究之一,就是在三年內跟蹤超過五千名Facebook用戶的行爲,研究發現,使用率上升,可能會導致用戶身體健康,心理健康和生活滿意度下降。
2017年11月的一次活動中,Facebook的第一任總裁肖恩·帕克稱自己是社交媒體的“盡責的反對者”,他說,“只有上帝知道它對我們孩子的大腦有什麼影響。”
幾天後,Chamath Palihapitiya,前任用戶增長副總裁告訴斯坦福大學的聽衆說,“我們創造的短期多巴胺驅動的反饋循環,正在摧毀社會的運作方式,沒有民間話語,沒有合作,只有虛假的信息,誤導的真相。”
Palihapitiya曾於2007年到2011年在Facebook工作,這位硅谷著名人物表示:“我感到極度內疚。我想我們都知道自己內心深處的想法。“他補充說,他不允許自己的孩子使用Facebook這種狗屎。”
爲此,Facebook很快通過聲明迴應道:“Palihapitiya於2011年就離開了公司,所以對現在的情況不算是瞭解。與六年前相比,現在的Facebook已經完全不同。”
今年3月,Facebook遭遇了更大的醜聞:《紐約時報》和英國《觀察家報》報道,有研究人員獲得了Facebook用戶的個人信息,並將其出售給了川普和共和黨僱用的諮詢公司劍橋分析(Cambridge Analytica),這家機構通過使用“心理”技術來操控選民的行爲。
也就是說,共計8700萬Facebook用戶的個人數據信息遭到了泄露。更爲誇張的是,Facebook早在2015年12月就已經發現了這個問題,但卻一直保持沉默,既沒有告知用戶,也沒有報備監管機構,而只是在媒體曝光之後才站出來承認了這件事。
劍橋分析的曝光,引發了Facebook歷史上最嚴重的危機,更是引起了廣大民衆對於大科技時代的反思甚至批判。
直到現在,Facebook都還處於美國聯邦調查局、證券交易委員會、司法部以及聯邦貿易委員會的調查之下。
此外,英國、比利時以及澳大利亞等外國政府機構,也紛紛要求Facebook作出解釋陳述。
另外,包括特斯拉和蘋果在內的科技同行們,也沒有對Facebook表現出任何同情。
特斯拉創始人埃隆·馬斯克刪除了名下多家公司的Facebook主頁,包括特斯拉和SpaceX。蘋果CEO蒂姆·庫克則在採訪中表示:“其實,對於科技公司來說,利用大量用戶數據信息來賺錢,是一件比較常見、比較容易的事情。但是,我們並沒有這樣做。”
5月舉行Facebook年度股東大會上,高管們努力維持秩序,情緒激動的投資者要求扎克伯格辭任董事長。
而在會場外面,一架飛機上掛着一條橫幅,上面寫着“你毀了民主”,這個廣告來源於公益組織“從Facebook獲得自由”,後者向美國證監會提議,要把涉嫌壟斷的Facebook進行拆分。
7月25日,Facebook的股價下跌了19%,市值減少了1190億元,這是華爾街歷史上最大單日跌幅。
《名利場》的科技作者尼克·比頓在推文中稱,扎克伯格每秒損失270萬美元,“這是美國人平均一生收入的兩倍。”
Facebook的用戶羣在美國和加拿大走平,在歐洲略有下降,高管警告稱,收入增長將進一步下滑,部分原因是醜聞導致用戶開始拒絕Facebook收集個人數據。
Facebook開始失去公衆的信任。
暖男馬克和“國王”扎克伯格
朋友們將這種艱辛和磨難描述爲扎克伯格成功的副產品。他被經常拿來與另一位哈佛輟學生比爾·蓋茨相提並論,後者也是小紮在商業和慈善事業的導師。
蓋茨告訴我,“但凡一個人聰明能幹、身家富有,出了問題之後卻不願意承擔責任,就會給人一種傲慢自大的感覺。但我要說,扎克伯格並不是這樣一種人。”
儘管如此,批評者依然認爲Facebook是一家被貪婪和利潤矇蔽雙眼的公司。
今年夏天,我們在扎克伯格家裏,辦公室和電話裏,進行了一系列的對話。我還採訪了公司內外的四十幾個人,瞭解其文化,扎克伯格的表現和決策。
我發現扎克伯格非常拘謹和緊張,那些沒有提前準備過的問題,他一般不會過多作答,包括真理的含義,言論自由的限制以及暴力的起源。
扎克伯格還引發了關於硅谷道德品質及其領導人良知的全面辯論。
斯坦福大學的科技史學家萊斯利·柏林告訴我,“長期以來,硅谷都享受了全美國敞開懷抱的接納。現在每個人都說,這是(硅谷的)詭計嗎?扎克伯格正在處理的問題是:我的公司應該成爲20億人對真理和體面的仲裁者嗎?從沒有人面對過這麼大的問題。”
Facebook的總部位於門洛帕克的Hacker Way1號。園區是個獨立的世界,提供硅谷全方位的免費服務:乾洗,理髮,音樂課和豐富的食物選擇,包括燒烤、沙拉、印度咖喱吧。
園區的設計者是迪士尼的顧問,類似一個人造小鎮,沿着主要街道設有商店,餐館和辦公室。從空中俯瞰,可以看到路面上的巨大的單詞“黑客”(HACK)。
在扎克伯格的園區裏,他就是國王。高管們對他過度讚賞,員工爲他遭受公衆誤解而打抱不平。
負責Facebook區塊鏈項目的大衛·馬庫斯告訴我,“當我看到他被批評時,我很心疼他,因爲他不是那樣子的。”
“他不是個混蛋,”一位前高管告訴我。 “這就是員工們留下來工作的原因。”
與出現在公共場合相比,私下裏扎克伯格是一個暖男。這讓人想起想起克林頓。
這兩個人的公衆形象和個人真實形象,有着相當大的差別。到目前爲止,他們還沒有找到一種方式來向公衆正確表達出自己真實想法、展現出自己的真實性格。
公開場合的扎克伯格,很少自我反思。去年春天,在接受美國CNN電視採訪後,他說他想建立一個“我的女兒在其中長大併爲我而自豪”的公司。CNN將這剪輯爲新聞事件,標題爲“扎克伯格罕見的情感流露”。
面對公衆的指責,扎克伯格似乎相當委屈。
“我不是最圓滑的人,一旦說錯話,代價很大”,他說,“所以,我並不想讓身邊的人來承受自己說錯話的後果。”
扎克伯格在公司內部的崇高地位,讓他很難傾聽到真實聲音,他有時試圖自己尋找真相。
2013年,他立下新年決議,他要每天認識一個並不是Facebook員工的新人。
2017年,他在一次“傾聽之旅”中前往美國三十多個州,希望更好地瞭解外面的世界。
奧巴馬總統前任競選經理大衛·普勞夫參加了這場巡迴之旅。他告訴我,“當一個政治家去其中一個地方時,會花一個小時,然後自說自話50分鐘。扎克伯格會說5分鐘,然後只是提問。”
但這場巡迴之旅,在公衆眼中,卻相當笨拙可笑。
一位專業攝影師記錄了扎克伯格在威斯康星州喂牛犢、訂燒烤,以及在密歇根州的福特工廠裝配線上工作的場景。
刻薄的網民說,這些照片讓他看起來像是外星人第一次探索人類。
參與此次巡演的前Facebook高管對朋友說,“沒有人想告訴馬克,也沒有人真得對馬克說,這看起來真的很蠢。”
扎克伯格近一半的生命都花在自己創辦的公司之中,親手挑選副手,建立公司制度,甚至Facebook的標誌性顏色皇家藍也反映了他的品味。扎克伯格是紅綠色盲,他選擇藍色是因爲他看得最清楚。
首席運營官謝麗桑德伯格告訴我,“有時馬克會在公司說,’好吧,我從來沒有在其他任何地方工作,但謝麗告訴我’…… ”她接着說,“他承認他沒有豐富的經驗。他只有他本人的經歷,而成爲馬克·扎克伯格是非常特別的。”
崇拜奧古斯都的中產男孩
早在看起來不可避免或者看似合理之前,扎克伯格就對自己的潛力有着充分認識。
他的老朋友說, “我認爲馬克一直認爲自己是一個有歷史意義的人,一個註定的偉人。”
扎克伯格發現,很多歷史巨人都是在大城市附近的小鎮長大,
在扎克伯格的故事裏,這個地方就是紐約的Dobbs Ferry,位於紐約市以北25英里的威徹斯特郡郊區。
他的母親Karen Kempner在皇后區長大,通過相親認識了正在學牙醫的Edward Zuckerberg。
他們結婚並生了四個孩子。馬克,唯一的男孩,排行老二。
馬克的母親是一名精神科醫生,她最終放棄了自己的職業生涯,照顧孩子並管理與家族所有的牙科診所。
扎克伯格的父親則是一名牙醫,但他也是一名十足的技術迷。Ed Zuckerberg將自己稱爲無痛博士Z,後來通過直郵推廣牙科,郵件上寫着是“我真是Facebook的父親!”
在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Ed購買了早期的個人電腦Atari 800以及I.B.M.XT,馬克藉此學會了編程。
十二歲的時候,他建立了自己的第一個網絡ZuckNet,可以在自己家裏和他父親的牙科診所之間共享信息和文件。
大衛·霍爾茲告訴我,他看扎克伯格和其它孩子在一起,感覺到他“超越了他的同齡人。他正在考慮其他人沒有想的事情。”
當我問扎克伯格的驅動力來自哪裏時,他追溯到他的祖父母,他們在二十世紀初從歐洲移民過來。 “他們過來,經歷了大蕭條,過着非常艱苦的生活,”他說。 “他們對孩子的夢想是,他們每個人都會成爲醫生,他們做到了,而我的母親總是相信我們應該有更大的影響力。”
他的大姐蘭迪,早期Facebook的發言人,已經開始寫書並主持一個廣播節目;唐娜從普林斯頓大學獲得博士學位,如今在編輯在線經典雜誌;阿麗兒曾在Google工作並擔任風險投資家。
當扎克伯格讀高三時,他轉學到菲利普斯埃克塞特學院,在那裏他大部分時間都在編程、擊劍和學習拉丁語。
從那時起古羅馬便成爲他終生的癡迷,首先是因爲語言(“它非常像編程或數學,所以我很欣賞”),然後是因爲歷史。扎克伯格告訴我,“我認爲奧古斯都是最迷人的角色。他通過嚴酷的統治建立了兩百年的世界和平。”
歷史上的奧古斯都,十八歲時建立自己的權力,征服了埃及,西班牙北部和中歐的大部分地區,並將羅馬從一個共和國變爲一個帝國。
他還消滅了政治對手,驅逐了他亂交的女兒,並安排處決了自己的孫子。
“哪有什麼權衡取捨?”扎克伯格激動起來, “一方面,世界和平是人們今天談論的長期目標,兩百年的和平相當難得。另一方面,(和平)不是免費的,他必須做某些事情。“
2012年,扎克伯格和陳在羅馬度過了他們的蜜月。他後來說,“我的妻子取笑我,說她認爲蜜月期間有三個人:我,她和奧古斯都。所有的照片都是奧古斯都的不同雕塑。“這對夫婦甚至將他們的第二個女兒命名爲August。
增長壓倒一切:窺視、操縱和抗議
2002年,扎克伯格到哈佛大學報到,在那裏他投身黑客精神追求破壞慶祝榮耀。 “那種對當權者來說’去你媽的’(氛圍)非常強大,”他的老朋友說。
2004年,作爲一名大二學生,他開始與四名同學一起成立Thefacebook.com(“the”在次年被去掉);所有權的法律糾紛,包括孿生兄弟卡梅倫和泰勒·溫克萊沃斯提起的訴訟,指責扎克伯格竊取他們的想法;隨之披露的令人尷尬的消息,其中扎克伯格嘲笑用戶給他這麼多數據(“他們’相信我’,愚蠢的人。”);他對這些言論表示遺憾,並在此後的歲月裏努力說服全世界他已經放棄了這種思維定勢。
在扎克伯格大學二年級期間,在派對等待上衛生間的時候,他遇到了大一新生Priscilla Chan。
她的父母追根溯源到中國,她在越南長大,戰後隨難民抵達美國,定居在馬薩諸塞州的昆西,在那裏他們爲中餐館洗碗謀生。
普麗西拉是三個女兒中最大的一個,也是家族裏第一個大學生。 “我突然去了哈佛,這裏有真正的知識分子,”她說, “然後我遇見了馬克。”
普麗西拉與扎克伯格的背景完全不同 ,“我的高中同學有一半去上了(社區)大學,後來出了一名木匠或機械師”。
出身的不同會導致一些隔閡,但是她說,”我必須儘早意識到我不會改變馬克。”
哈佛畢業之後,陳在一所小學任教並最終成爲一名兒科醫生。 2017年,她不再行醫,迴歸家庭。
當我問陳有關扎克伯格如何迴應公衆批評時,她說 “他真得坐了太長時間,以至於他的肌肉收縮,傷了他的臀部。”
大二之後,扎克伯格搬到了帕洛阿爾託,然後就此定居。
扎克伯格攜帶兩套名片。一個寫得是“我是CEO……婊子!”參觀者會遇到一個騎着羅威納犬的衣着暴露的女人的塗鴉壁畫。在Adam Fisher關於硅谷的口述歷史“天才之谷”中,一位名叫Ezra Callahan的早期員工沉思道,“‘互聯網的方向在多大程度上受到這羣19,20,21歲的富裕的白人男孩影響呢?”
Facebook推出時很幸運:硅谷正從互聯網泡沫破滅中復甦。
互聯網基本上不受監管;先行者可以積累大量的追隨者並鞏固權力,而廉價智能手機的崛起吸引了數百萬新用戶;沒有隱私意識的用戶,交出大量個人信息,而且是免費的。
增長小組的創始成員亞歷克斯舒爾茨說,他和他的同事們在追求擴張方面都很狂熱。 “你會爲那寸土而戰,你會爲那寸土而死,”他告訴我。
Sandy Parakilas於2011年加入Facebook,擔任運營經理,“我們相信增長宗教。”他說,“增長團隊是最酷的。”
爲了獲得更大的覆蓋,Facebook做出了致命的決定,對外開放大量數據。
在Facebook工作幾個月後,Parakilas發現,有些遊戲會讀走用戶的信息和照片。他說,有個案例裏,開發人員收集用戶信息,包括兒童信息,以便在自己的網站上創建未經授權的個人資料。Facebook在沒有系統檢查濫用之前,就已經對外開放了數據。 Parakilas建議立刻審計問題的嚴重性,但是,他被一位高管拒絕了,因爲公司都在關注“增長”。
新員工瞭解到,衡量公司業績的一個關鍵指標,是有多少用戶在過去7天中有6天登錄了Facebook,這一標準被稱爲L6 / 7。
“你可以說,這是有多少人喜歡這項服務”,2012年離開公司的Parakilas表示。
“但是,如果這是你的工作目標,你開始考慮‘嗯,我可以用什麼黑暗模式讓人們重新登錄?’”
通過調整虛榮,激情和易感性的槓桿,Facebook工程師成爲了一種新的行爲主義者。 2012年,當陳在醫學院時,她和扎克伯格討論了器官移植的嚴重短缺,啓發了扎克伯格在Facebook上添加一個小的功能:如果人們透露他們是器官捐獻者,這個消息自動向好友發送通知,在該功能出現的第一天,它在全國範圍內增加的官方器官捐獻者翻了二十倍。
緊接着,Facebook也擁有了影響選民政治行爲的能量。
研究人員發現,在2010年中期選舉期間,Facebook能夠通過向他們展示已經投票的朋友的照片,並讓他們選擇點擊“我投票”按鈕來刺激用戶投票。這項技術使得投票量提高了34萬人,是2016年同期數據的四倍多。
它成爲員工熟悉的競選笑話——Facebook可以通過選擇在哪裏部署“我投票”按鈕來推動選舉、改變選舉結果。
這些能力可能會被濫用。 2012年,Facebook數據科學家將近七十萬人當作實驗小白鼠,爲他們提供快樂或悲傷的帖子,來測試情緒在社交媒體上是否具有傳染性。 (他們得出的結論是確實有傳染性。)
當研究結果發表在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刊中,引起了用戶的騷動,許多人都驚恐地發現他們的情緒可能被偷偷摸摸地操縱了。
用谷歌前設計倫理學家特里斯坦哈里斯的話說,Facebook正成爲“說服技術”的先驅。
扎克伯格和其他高管最終發現,即便用戶最初會反對,但他們最終依然會接受改變的發生。
2006年,Facebook推出了新聞流,該功能在用戶更改個人資料圖片,加入羣組或更改關係狀態時會突然提醒朋友,這在公司總部發生了一場街頭抗議活動,成千上萬的人加入了一個反對變革的Facebook小組。
扎克伯格發佈了一個不溫不火的道歉(“冷靜下來。呼吸。我們聽到你了。”),但最終,人們最終習慣了新聞流。
2006年,扎克伯格在這家初出茅廬的公司做出了最不受歡迎的決定。雅虎出10億美元收購Facebook,而當時的高級助手馬特·科勒回憶道,“我們的增長已經停滯不前。”科勒和其他許多人懇求扎克伯格接受這一提議,但他拒絕了。
“幾乎所有高管都對他和業務失去了信心,”科勒說。
接下來,大多數高管都在十八個月內離開了,扎克伯格說,“完全崩潰了,但我從中學到,如果你堅持自己的價值觀,那麼你就能度過難關。有時它需要些時間,你必須重建,但這是非常有力的一課。”
有幾次,扎克伯格在涉及隱私的問題上跌跌撞撞。2010年,他說隱私不再是一種“社會規範”。
那一年,公司在默認公開大多數用戶信息後,再次發現自己陷入困境,聯邦貿易委員會譴責Facebook“採取了不公平和欺騙性做法”。
扎克伯格不得不簽署了一項同意法令,承諾建立一個“全面隱私計劃”,並在接下來的二十年每隔一年都對其進行全面評估,“我認爲有少數高調的錯誤……使我們所做的大部分工作都蒙上陰影。”
Facebook有句海盜格言,即“快速行動,打破局面”(move fast and break things),這種格言標誌着這樣一種觀點,即最好是有缺陷的第一名而不要小心謹慎和追求完美。
安德魯·博斯沃思(Andrew Bosworth)曾是哈佛大學的助教,現在是扎克伯格任職時間最長的副手之一,他解釋說:“失敗可能是一種成功的形式。這不是你想要的形式,但它對你如何學習是有用的。”
在扎克伯格看來,懷疑論者往往只是頑固守舊和謾罵而已。 “總會有人想讓你慢下來,”他在去年哈佛大學的畢業典禮上說道。 “在我們的社會中,我們經常不做大事,因爲我們害怕犯錯誤,如果我們什麼也不做,我們就會忽視今天所有錯誤。實際情況是,我們所做的任何事情都將在未來出現問題。但這不能阻止我們開始行動。”
2012年,扎克伯格爲Instagram支付了10億美元,該公司當時只有13名員工。
公衆批評這個收購價太高了,但它被證明是互聯網歷史上最好的投資之一。
今天,Instagram的價值是扎克伯格爲其支付的價值的一百倍以上,更重要的是,它受年輕人歡迎,這一羣體對Facebook的興趣在不斷下降。
那年春天,Facebook在納斯達克上市,估值爲一千零四億美元。
上市當天出現技術故障,許多人懷疑公司被高估了。股價迅速下挫。華爾街日報稱這場IPO是場“慘敗”,股東開始起訴Facebook和扎克伯格。
“我們受到了很多批評,”他回憶道。 “我們的市值減少了一半。但我堅信我們做的是正確的事情。“(即使最近暴跌,Facebook股票的價值比IPO時上漲超過四倍。)
扎克伯格爲公司實現逆勢擴張而倍感自豪。
2011年,當用戶開始從臺式電腦轉向手機時,Facebook也開始了移動話轉型。
扎克伯格告訴員工,對轉型沒有貢獻者會被趕出辦公室。博斯沃思回憶說:“在一個月之內,如果你沒有拿出移動端的產品,你真的無法與馬克會面。”
2014年,隨着問題的積累,Facebook改變了其座右銘,從“快速行動,打破局面”變成了低調的“用穩定的基礎架構快速行動。”
儘管如此,在內部,創業精神仍然存在。
失控:助力暴亂和騷動
2016年初,扎克伯格指示員工加速發佈視頻流服務Facebook Live,並將其工程團隊從12個擴展到100多個。
但問題接踵而至,Facebook Live視頻裏呈現了人們自殺或從事犯罪的活動,在審覈者發現並下架視頻之前,就開始廣泛流傳。服務推出幾個月後,一位名叫安東尼奧·帕金斯的芝加哥男子在Facebook Live上被槍 殺,視頻被觀看了數十萬次。
這一事件本應成爲減速的警告。但是,第二天,博斯沃思發送了一份值得注意的內部備忘錄,證明Facebook“醜陋”的社會影響是增長所必需的權衡代價:“任何能讓我們更頻繁地連接更多人的事情都是*事實上*的好事。”
今年春天,在備忘錄被泄露給BuzzFeed之後,博斯沃思說他一直在扮演魔鬼的擁護者,扎克伯格發表聲明:“波茲是一位才華橫溢的領導者,他說過許多挑釁性的事。這是包括我在內的Facebook大多數人強烈不同意的觀點。”
隨着Facebook的海外擴張,它的盲點也在擴大。
該公司的未來發展,依賴於發展中國家的增長,但該平臺已成爲全球脆弱地區引發暴力的強大催化劑。
在旗下產品WhatsApp的最大市場印度,惡作劇引發了騷亂,私刑和致命的毆打。無奈的當地官員在去年一年提出了六十五次關閉互聯網的請求。
在利比亞,人們利用Facebook交易武器。在斯里蘭卡,佛教暴徒今年春天因謠言襲擊了穆斯林,一位總統顧問告訴《紐約時報》,“問題出在我們身上,但Facebook在煽風點火。”
緬甸的損傷最爲嚴重,穆斯林少數民族遭受殘酷的殺戮,羣奸和酷刑。2012年,該國約有1%的人口可以上網。三年後,這一數字達到了25%。在當地,智能手機通常預裝了Facebook應用程序,佛教極端分子試圖通過謠言信息,煽動種族緊張局勢。 Wirathu是一名擁有大量Facebook追隨者的僧侶,他在2014年引發了一場針對穆斯林的致命騷亂,當時他分享了一份關於強姦的虛假報告,並警告說“異教徒在對抗我們”。
從2013年開始,緬甸的一系列專家與Facebook官員會面,警告他們正在助長襲擊。
緬甸的企業家大衛·馬登向官員們做了次演示,指出Facebook類似於在盧旺達種族滅絕期間傳播仇恨的無線電廣播。
Facebook高管迴應說,他們正在招聘更多的緬甸語網管來下架危險內容,但該公司一再拒絕透露實際僱用了多少人。
直到去年3月,情況變得嚴峻:近一百萬羅興亞人逃離緬甸。
聯合國認爲這是一場種族滅絕,負責調查危機的聯合國調查員說,“我擔心Facebook現在變成了一頭野獸,違背了它的初心。”
隨後,當被質詢時,扎克伯格重申了Facebook“招聘數十名”緬甸語內容審稿人的說法。
三個多月後,我問了緬甸技術中心Phandeeyar的CEOJes Kaliebe Petersen ,緬甸有什麼進展沒有。 “我們沒有看到Facebook的任何實質性變化,”他告訴我。 “我們不知道有多少人在Facebook上講緬甸語。這裏的情況越來越糟。“
第二天早上我看到扎克伯格,爲何爲何沒有進展。他回答說:“是的,我認爲緬甸局勢非常糟糕。”
他逃避了我的問題,我繼續追問,緬甸人不相信一家擁有Facebook資源的公司會注意不到他們的抱怨。
“我們會認真對待這件事,”他說。 “你不能只是打個響指就解決這些問題。僱用人員並培訓他們需要時間,還需要建立可以爲他們標記內容的系統。”
他承諾Facebook將在年底之前僱傭“一百個或更多緬甸人“,並補充說, “我對我們的進展不滿,我們並沒有像我們想得那樣快速行動。”
在我們談話幾周後,Facebook宣佈它封禁了緬甸陸軍總司令和其他幾名軍官賬號。
多年來,扎克伯格將他拒絕抱怨的能力視爲美德。但到2016年,這種立場引發了公司危機。
倫理學家特里斯坦•哈里斯(Tristan Harris)說:“當你掌管像Facebook這樣的公司時,你會一直受到批評,如果很多批評都沒有根據,你就會停止關注批評。”他繼續說道,“問題是它也讓你脫離了真正有價值的批評。”
是否操縱了大選
2016年的選舉本應對Facebook是件好事。那年1月,謝麗·桑德伯格告訴投資者,選舉將在“廣告支出方面帶來大單子”,可與超級碗和世界盃相媲美。
根據研究和諮詢公司Borrell Associates的說法,候選人和其他政治團體有望在選舉中耗費14億美元,比四年前增加了9倍。
Facebook提議在總統競選辦公室免費“嵌入”員工,以幫助他們有效地使用該平臺。
克林頓的競選活動拒絕了嵌入員工。川普說好,於是Facebook的員工幫助他的競選活動製作了消息。
雖然川普的語言公開敵視少數民族,但在Facebook內部,他的行爲對於高管來說,就像華盛頓遙遠的污水池的一部分,並不會讓他們感到發自肺腑的不適和反感。
在競選期間,川普使用Facebook籌集了2.8億美元。大選前幾天,他的團隊支付了Facebook平臺上的選民操縱費用。
據《彭博商業週刊》報道,它針對的是三類民主黨選民: “理想主義的白人自由主義者,年輕女性和非洲裔美國人” ,向他們定向發送精心定製的視頻,以阻止他們爲克林頓投票。川普競選活動的數字內容總監特蕾莎·洪(Theresa Hong)後來告訴採訪者,“沒有Facebook,我們就不會贏。”
大選過後,Facebook高管們擔心公司將因爲傳播假新聞備受指責。
扎克伯格的工作人員向他提供了統計數據,顯示該平臺上的絕大多數選舉信息都是合法的。
幾天後的一次技術會議上,扎克伯格自我辯護說: “認爲Facebook上的假新聞以任何方式影響選舉的想法,我認爲這是個非常瘋狂的想法”,他說。
扎克伯格的自我辯護,讓公司高管們感到震驚。一位前高管告訴《連線》,“我們必須提醒他,否則,公司就會沿着這條賤民路(pariah path)上走下去。”
當我問起扎克伯格時,他反思他當時的辯解是錯的,“沒有人想要任何劑量的假新聞,我們需要認真對待這個問題。”
但他仍然對Facebook可能扭曲選民行爲的暗示感到憤怒。他說:“這種觀點,人們只會被欺騙投票,這是對我的冒犯。每個用戶都很聰明,能夠根據自己的經驗,做出正確的選擇。”
大選後不久,參議院情報委員會民主黨人馬克·華納與Facebook聯繫,討論俄羅斯的干涉問題。 “最初的反應是完全不屑一顧,”他告訴我。但是,到了春天,他感覺公司意識到它出了嚴重的問題。 “他們在法國大選中看到了大量的俄羅斯人行爲,”華納說。 “情況正在好轉,但我仍然認爲他們沒有把足夠的資源投入其中。”在電信業務上發了大財的華納補充說,“硅谷的大多數公司都認爲政策制定者首先是搞不明白,其次是最終看下來,如果他們只是阻止我們,那我們就走。”
Facebook斷斷續續承認了它在選舉中扮演的角色。 2017年9月,在Robert Mueller獲得搜查令後,Facebook同意向他的辦公室提供與俄羅斯相關的廣告清單以及誰支付了這些廣告的詳細信息。
10月,Facebook透露,俄羅斯特工已經發布了大約8萬個帖子,觸及1.26億美國人。
三月份,在劍橋分析的新聞爆發後,扎克伯格和Facebook陷入癱瘓。連續五天,扎克伯格什麼話都沒說。他個人的Facebook頁面沒有提供任何陳述或分析。它的最新帖子是他和Chan爲Purim做烘焙的照片。
“我覺得我們讓人們失望,這感覺非常糟糕,”他後來告訴我。 “但它又回到這個觀念,即我們不應該多次犯同樣的錯誤。”他堅持認爲假新聞不像人們想象的那麼普遍,他仍然不相信錯誤信息的傳播會對選舉產生影響。 “我實際上並不認爲這是一件蓋棺定論的事,”他說。 “我仍然認爲這是需要研究的事情。”
在談話中,扎克伯格毫無疑問是高度分析性的。
當他遇到一種與自己觀點不同的理論時,他會發現一處分歧 ,一處事實,一個方法論,一個前提,然後猛錘這點。這是贏得爭論的有效技巧,但卻難以接入新的信息。
一位前Facebook高管說,“他們只想聽到好消息,他們不希望聽到那些不同意他們的人。有種文化是’你要服從,才能一起走。’”
我曾經問過扎克伯格他讀什麼來獲取新聞。 “我可能主要靠閱讀聚合器,”他說,“真的沒有什麼報紙讓我拿起來從頭讀到尾。大多數人都沒有讀過實體報紙了,但是我瀏覽的新聞網站並不多。”
扎克伯格和桑德伯格將他們的錯誤歸咎於過度樂觀,看不到那些負面的黑暗應用。扎克伯格拒絕圍繞對隱私的新理解來重新組織公司,或重新考慮其爲廣告商收集的數據深度。
James P. Steyer是常識傳媒的創始人兼CEO,這是家促進兒童技術和媒體安全的組織,他2018年春季訪問了Facebook的總部,討論了他對名爲Messenger Kids的產品的擔憂,該產品允許13歲以下兒童(這是使用Facebook應用的最低年齡)進行視頻通話並向父母批准的聯繫人發送消息。
他見到了桑德伯格以及當時的政策和溝通負責人Elliot Schrage。 “我尊重他們的商業成功,就像謝麗一樣,我希望他們最終可以考慮採取措施更好地保護孩子。相反,他們說對年幼孩子來說最好的事情就是花更多時間在Messenger Kids上。
一些員工認爲,Facebook高管似乎不是在集中精力解決問題和預防問題,而是集中精力來壓制問題引發的負面輿論。
谷歌前民意測驗專家塔維斯麥金恩於2017年春季開始在Facebook工作,他的民意調查範圍很窄:衡量公衆對扎克伯格和桑德伯格的看法。
在接下來的六個月裏,麥金恩在三個國家進行了八次調查,包括扎克伯格的寫作,照片,甚至是他在後院燒烤的直播。
9月,麥金恩辭職。在一次採訪中,他告訴Verge網站說自己已經灰心喪氣,“我無法改變它的價值觀。我無法改變這種文化。我對告別別人我在Facebook工作也不自豪。我不覺得自己在幫助這個世界。”
從創新者到壟斷者:Great or Good?
三月份,扎克伯格同意在國會首次就Facebook處理用戶數據作證。聽證會定於4月舉行。隨着日期臨近,聽證會有了庭審的弦外之音。
在不到兩年的時間裏,華盛頓的情緒發生了變化。互聯網公司和企業家以前被認爲是美國獨創性的先鋒和時代的宇航員,如今他們正被拿來與與標準石油公司和其它鍍金時代的壟斷者相比較。
今年春天,《華爾街日報》發表了一篇文章,開頭說:“想象一下,在一個不太遙遠的未來,其中的反壟斷強迫Facebook出售Instagram和WhatsApp。”
它伴隨着一幅棕褐色的插圖,有扎克伯格,蒂姆庫克和其他技術首席執行官已被嫁接到引發聯想的強盜貴族的過度膨脹軀幹上。
1915年,改革者和未來的最高法院大法官路易斯·布蘭代斯在國會委員會面前作證,論證足以使公司達到一種近乎主權的水平的危險性。“如此強大,以至於現有的普通社會和工業力量不足以對付它,他稱之爲“大的詛咒”。哥倫比亞法學院教授蒂姆·吳(Tim Wu)即將出版一本書,靈感就來自布蘭迪斯的一句話,他告訴我,“今天,再也沒有比大科技更能說明大對民主的威脅了。“他補充說,”當一個集中的私人權力對我們所看到和聽到的東西有這樣的控制權時,它就擁有可以媲美或超過民選政府的權力。”
在扎克伯格要作證之前不久,華盛頓WilmerHale律師事務所的一個團隊飛到門洛帕克,通過模擬聽證會指導他,並指導他做出必要的謙卑姿態。
甚至在最近的醜聞發生之前,比爾·蓋茨就曾建議扎克伯格對立法者的意見保持警惕,這是蓋茨在1998年微軟面臨壟斷行爲指控時所吸取的教訓。蓋茨蔑視地向國會證實,“計算機軟件行業並沒有衰敗,也沒有必要解決這個問題。”
幾個月內,司法部起訴微軟違反聯邦反托拉斯法,在達成和解之前經歷了三年的法律痛苦。蓋茨告訴我,他後悔“嘲弄”監管機構,說:“那不是我會選擇重複去做的事。”他鼓勵扎克伯格關注華盛頓DC。
“我說,‘在那開個辦公室,現在就開。‘而馬克做了,他欠我的,”蓋茨說。去年,Facebook斥資1150萬美元在華盛頓進行遊說,這個數字排在美國銀行家協會和通用動力公司之間。
4月10日,當扎克伯格到達參議院聽證會時,他穿着一身深藍色的西裝,坐在四十多名參議員面前。
在他面前,他的筆記概述了可能的問題和答案,包括參議員可能要求他卸任離開公司的前景。簡單來說,他的回答是:“成立了Facebook。我的決定。我犯了錯。很大的挑戰,但我們之前解決過問題,馬上要解決這個問題。已經採取行動。”
事實證明,沒有人要求他辭職,也沒什麼難回答的問題。儘管有些時候有壓力,但聽證之後留下的壓倒性印象是,一些參議員理解這些問題的能力有多差。
一個感悟時刻來自猶他州的八十四歲共和黨人奧林•哈奇(Orrin Hatch),他要求知道如果“用戶不爲你的服務付費,Facebook會如何賺錢。”扎克伯格帶着一點微笑回答說,“參議員,我們有廣告的 ”。
對傾向於不信任扎克伯格的觀察者來說,他已經迴避到健忘症的狀態,他說了四十多次他需要跟進,但聽證會五個小時之後,他毫髮無傷,密切關注的華爾街通過將Facebook股票的市值提高200億美元來獎勵他。
幾天後,在Facebook的內部留言板上,一名員工計劃購買T恤,上面寫着“參議員,我們有廣告的”。
當我問扎克伯格政策制定者是否可能拆散Facebook時,他堅決地回答說,這樣的舉動將是個錯誤。他告訴我,這個領域“極具競爭力”。
“我認爲有時候人們會進入這種模式‘嗯,沒什麼能確切替代Facebook的。’實際上,這使它更具競爭力,因爲我們真正是在一個不同的系統:我們和Twitter競爭;我們與Snapchat競爭;我們做消息傳遞,但iMessage默認安裝在每一部iPhone上。“他承認更深層次的擔憂。 “還有另一個問題,那就是,除了法律之外,我們對這些科技公司這麼大有什麼看法?”他說。
他認爲,“縮減”Facebook或其他硅谷重量級人物增長的努力將把這個地盤拱手交給中國。他說:“我認爲,我們所做的任何限制的事情,首先會對我們在其他地方的成功產生影響。大體上來說,在短期內我不會擔心中國公司或其他任何公司會在美國獲勝。但是在東南亞,歐洲,拉丁美洲以及許多不同的地方,所有這些地方都存在日常競爭激烈的局面。”
華盛頓的粗略共識是監管機構不太可能試圖拆解Facebook。 FTC幾乎可以肯定對公司違規行爲罰款,並可能會考慮阻止它購買大型潛在競爭對手,但前FTC專員告訴我,“在美國,你可以獲得壟斷地位,只要你是在不做違法的情況下實現壟斷並維持住。”
Facebook正在歐洲遭遇更嚴厲的待遇,歐洲的反壟斷法更加強大,法西斯主義的歷史使人們特別警惕侵犯隱私的行爲。
對硅谷最強大的批評者之一是歐盟頂級反壟斷監管者Margrethe Vestager。去年,在對谷歌的搜索引擎進行調查後,Vestager指控該公司給其購物服務“非法優勢”並罰款27億美元,當時是歐盟反壟斷法最大的罰款。 7月,她又爲Google要求設備製造商預裝Google應用程序的做法增加了50億美元的罰款。
在布魯塞爾,Vestager很高調,近六英尺高,梳着黑色和銀色的短髮。她在丹麥農村長大,是一位路德教牧師的長女,當我最近與她交談時,她用哲學術語談到了她的執法權力。 “我們正在處理的事情,是當人們開始做違法的事情,那像亞當和夏娃一樣古老,”她說。 “人類的決定經常受到貪婪的指導,害怕被擠出市場,或者失去對你很重要的東西。然後,如果你把力量投入到貪婪和恐懼的混合物中,你就會有一些可以隨時識別的東西。”
Vestager告訴我,她的辦公室目前沒有涉及Facebook的案件,但她對公司正在利用用戶表示擔憂,從她稱之爲“不平衡”的服務條款開始。她將這些條款解釋爲“這是你的數據,但是你給了我們一個全球免版稅的許可,基本上讓我們可以做我們想做的任何事。“想象一下,她說,如果實體店要求複製你的所有照片,用來做無限制,未指定的用途。 “你的孩子,從第一天到死亡,婚禮的排練晚宴,婚禮本身,第一個孩子受洗。你永遠不會接受(這樣的實體店要求),“她說。 “但是如果是數字版本協議的話,你在眨眼之間接就同意了。”
在Vestager看來,一個健康的市場應該讓Facebook產生競爭對手,將自己定位爲道德上更好的選擇,收集更少的數據並尋求更小的用戶關注度。她說:“我們需要社交媒體,讓我們擁有一個非上癮,無廣告的空間。”
“如果客戶喜歡您的產品,那麼您會非常受歡迎,並且會大大超過您的競爭對手。但是,如果你成長壟斷,你有責任不要濫用你的支配地位,使其他人很難與你競爭並吸引潛在客戶。當然,我們會密切關注它。如果我們開始擔心,我們會開始尋找(答案)。”
隨着Facebook的壓力越來越大,該公司一直在努力修復其漏洞。
12月,在Sean Parker和Chamath Palihapitiya公開談論社交媒體的破壞性心理影響之後,Facebook承認有證據表明大量使用會加劇焦慮和孤獨感。
經過多年完善的上癮功能,如“自動播放”視頻,它宣佈了一個新的方向:它將提升網站上花費的時間的質量,而不是數量。該公司修改了其算法,以強調來自朋友和家人的更新,這種內容最有可能促進“積極參與”。扎克伯格寫道,“我們確保在Facebook花的時間很值。”
該公司還在努力解決它再次成爲選舉季宣傳洗腦工具的可能性。在2018年,數億人將參加世界各地的選舉投票,這包括美國的中期選舉。經過多年遊說反對披露政治廣告資金來源的要求,該公司宣佈,用戶現在可以查找誰支付了政治廣告,廣告針對誰,以及資助者的其他廣告。
負責Facebook“選舉誠信”工作的產品經理Samidh Chakrabarti告訴我,關於俄羅斯互聯網研究機構的披露令人深感震驚。 “這不是我們任何人認爲我們正在努力的那種產品,”他說。隨着中期的臨近,該公司發現,俄羅斯人利用Facebook的模式激發了一代同樣關注政治辯論傾向的新演員。 “有很多模仿者,”Chakrabarti說。
扎克伯格曾經對“無摩擦共享”(frictionless sharing)的優點讚不絕口,但是現在Facebook正在努力“施加摩擦”以減緩虛假信息的傳播。
今年1月,該公司聘請了奧巴馬總統國家安全委員會前網絡安全政策主管納撒尼爾·格萊歇爾(Nathaniel Gleicher),以削弱“信息業務”。
7月,該公司刪除了32個賬戶,這些賬戶開展了可追溯到俄羅斯的虛假宣傳活動。幾個星期後,它刪除了超過六百五十個賬戶,小組和頁面,這些都能追溯到俄羅斯或伊朗。
儘管遏制選舉宣傳洗腦很難,扎克伯格最棘手的問題可能在於其他地方——在Facebook上出現意見的鬥爭中,哪些能出現,哪些不能,以及誰來決定。
作爲一名工程師,扎克伯格從不想涉足內容領域。最初,Facebook試圖阻止某些類型的材料,例如裸露的帖子,但它被迫創建了很長的例外列表,包括母乳餵養的圖像,“抗議行爲”和藝術作品。一旦Facebook成爲政治辯論的場所,問題就爆發了。今年4月,在與投資分析師的一次電話會議中,扎克伯格悶悶不樂地說“用A.I.去識別乳頭要比識別什麼是仇恨言論容易多了。 ”
對增長的狂熱導致了“大的詛咒”:每天,超過10億貼文在Facebook上發佈。
在任一時刻,Facebook“內容協調人”正在決定比如斯里蘭卡的一個帖子是否符合仇恨言論的標準,或者是否有關於韓國政治的爭議已經越界成爲欺凌。
扎克伯格試圖避免封禁用戶,寧願成爲“所有想法的平臺。”但他需要阻止Facebook陷入惡作劇和濫用的泥沼。他的解決方案是禁止“仇恨言論”但對“錯誤信息”施加較小的懲罰,這種廣泛的類別包括粗俗欺騙和簡單錯誤。
Facebook試圖制定關於如何應用懲罰的規則,但每個特殊情況都會引發更多規則,並且隨着時間的推移規則堆得山高。
根據《衛報》報道,去年Facebook發佈的培訓幻燈片,主持人被告知可以說“你真是個猶太人!”,但不允許說“愛爾蘭人是最好的,但法國人真的很糟糕”,因爲後者正在定義另一個人爲“劣等”。用戶不能寫“移民是人渣”,因爲它是非人性化的,但他們可以寫“讓飢渴的青少年移民遠離我們的女兒。”這些區別是通過神祕公式解釋給受訓者的,類似“未受保護+準受保護=未受保護”。
7月,這個問題不可避免地落在了扎克伯格身上。
多年來,Facebook爲陰謀理論家亞歷克斯·瓊斯提供了一個平臺,他的妄想包括在桑迪·胡克學校大屠殺中遇害的兒童的父母都是付費演員,目的是要禁槍。
Facebook不願意禁止瓊斯。當人們抱怨他的行爲違反了針對騷擾和假新聞的規定時,Facebook試驗了懲罰。起初,它“減少”他(的曝光),通過調整算法,他的消息將顯示給更少的人,同時向他的粉絲展示反駁他的斷言的文章。
然後,在7月下旬,諾亞波茲納是一個在桑迪·胡克遇害的孩子,他的父母倫納德·波茲納和維羅妮·克德拉羅薩發表了一封致“親愛的扎克伯格先生”的公開信,其中他們描述了被陰謀論者的死亡威脅不得不“東躲西藏的生活”,爲了有最基本的保護“與Facebook一場幾乎不可理解的戰鬥”。
在他們看來,扎克伯格“認爲對我們的攻擊是無關緊要的,提供援助來消除威脅太麻煩了,我們的生命不如爲仇恨提供安全的避風港更有價值。”
Facebook在某種程度上讓步了。
在7月27日,它下架了瓊斯的四個視頻,暫停了他賬號一個月.但公衆壓力並未放鬆。
8月5日,在蘋果公司表示該公司“不會容忍仇恨言論”後大壩崩塌,蘋果停止發佈與瓊斯有關的五個播客。
Facebook因“反覆”違反反對仇恨言論和欺凌的規定而關閉瓊斯的四個主頁。我問扎克伯格爲什麼Facebook在處理這種情況時動搖了。他對這個提議很生氣:“我不相信禁止一個人說出事實上不正確的事情是正確的。”
我說,瓊斯似乎不僅僅是事實上不正確。
“好吧,但我認爲這裏的事實非常明確,”他說道。“最初的問題是關於錯誤的信息。”他補充說,“除非直接煽動暴力行爲,否則我們不會將其取消並封號。”他告訴我,在瓊斯減少曝光之後,更多關於他的投訴涌入,提醒Facebook更老的帖子,並且公司正在辯論當蘋果宣佈禁令時應該做什麼。
這不是最後的窘境。 Facebook的言論自由困境沒有簡單的答案。
看到公司有強大的權力去選擇禁聲的時候,你不必非得成爲亞歷克斯·瓊斯的粉絲纔會氣餒,對這件事來說,去放大,去控制我們看到,聽到和所體驗的。
扎克伯格希望建立一個可擴展的系統,一個有序的決策樹,解決每一個可能性和異常狀況,但語言的邊界是一個困擾。
最高法院在定義色情時選用的是“當我看到它時我就知道了。”目前,Facebook正在使用Rube Goldberg機制制定政策和即興處理,而機會主義者則對此卻冷嘲熱諷。
德克薩斯州共和黨參議員泰德·克魯茲(Ted Cruz)抓住瓊斯的禁令,將之視爲對保守派進行的法西斯式襲擊。在一個甚至以克魯茲的標準來都有富餘的時刻,他引用了馬丁·尼莫勒關於大屠殺的着名臺詞,他說,“隨着這首詩的發展,你知道,’首先他們來抓亞歷克斯·瓊斯。‘”
桑德伯格上週在參議院情報委員會作證時說:“我們現在有超過兩萬人,我們每天二十四小時能夠用五十種語言審查報告。”(在會議開始前的走廊裏,彷彿爲了強調未來的複雜性,亞歷克斯·瓊斯已經開始表演,指責參議員馬克·盧比奧沒有采取更多行動讓他回到Facebook上。)
近年來,桑德伯格因其在公司外的工作而聞名,包括她的書籍關於女性賦權的《Lean in》以及在她的丈夫Dave Goldberg突然去世後寫作的《Option B》。但她對Facebook影響力的責任可能會增加,她作爲COO的聲譽也取決於變革的實施。
硅谷的許多人認爲桑德伯格和Facebook的董事會必須採取更多措施來阻止該公司再犯一個重大錯誤。
“我知道有幾個色盲的人,”一位著名高管對我說,“如果他們不想每天出門看起來像小丑Bozo一樣的話,他們的妻子會在早上爲他們穿衣服。謝麗和董事會應該爲馬克準備好衣服。“他接着說,”如果你有盲點,那麼你得依靠周圍的人來告訴你他們在哪裏。
在我們的一次談話中,我問扎克伯格,當人們質疑他缺乏情感時,他是否會覺得侮辱。 “侮辱?”他問道,然後停了幾秒鐘考慮。 “我覺得這不是侮辱。我不認爲這是準確的。我的意思是,我當然很關心。關心和讓情緒驅使下做出衝動的決定之間存在差異。”他繼續說道,“最後,我認爲我們做這個成功的事情的原因是因爲我們在不停的解決問題,通常你這樣做的時候靠的不是衝動、情緒化的決定。”
扎克伯格的漫畫是一個自動機器,對他工作的人文面向毫不在乎。事實是另一回事:像奧古斯都一樣,他用權衡換取和平狀態。
在言論和真相之間,他選擇了言論。在速度和完美之間,他選擇了速度。在規模和安全之間,他選擇了規模。到目前爲止,他的生活使他確信他能解決“一個接一個的問題”,無論公衆可能就此發出怎樣的嚎叫。
在某個時刻,扎克伯格上升期的心態習慣將開始對他不利。爲了避免進一步的危機,他將不得不接受這樣一個事實,即他現在是和平的保護者,而不是破壞它的人。
Facebook在勸說方面的巨大力量帶來了財富,也帶來了危險。無論喜歡與否,扎克伯格都是看門人。 Facebook可以通過實踐學習並在隨後修復錯誤的時代已經結束。這樣的成本太高,理想主義也不能爲做事疏忽辯護。
從某種意義上說,“馬克·扎克伯格製造” (他早年這樣稱呼Facebook)纔剛剛開始,扎克伯格還不到三十五歲。
問題不在於扎克伯格是否有能力修復Facebook,而是他是否有意願這樣做;他是否會將人們趕出他的辦公室,如同他當年帶領公司轉型移動時的熱情那樣,如果人們沒有向他提出防止緬甸暴力、保護隱私或者減輕社交媒體毒性的建議,他是否也會把他們都踢出辦公室。
很久以前,他已成功地讓Facebook很偉大(Great)。現在面臨的挑戰是讓它變好(Good)。